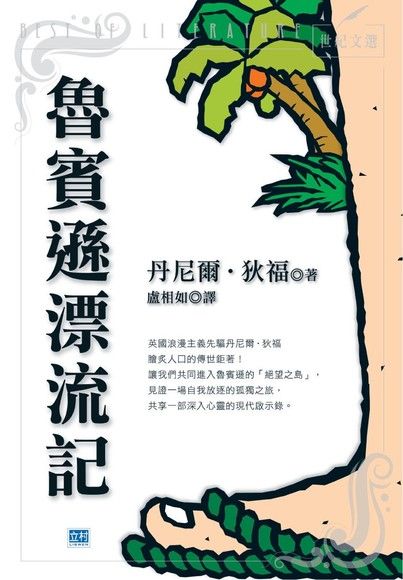大疫年紀事
第一本瘟疫文學,則當非以《魯賓遜漂流記》聞名的狄福(Daniel Defoe, 1660-1731)所著的《大疫年紀事》(A Journal of the plague year)莫屬,它可能是第一部以瘟疫為主題的小說創作。它寫的是一六六五年的倫敦鼠疫,那次鼠疫也橫掃了全歐。
狄福在之舉學上乃是「第三人稱現在式」這種紀實文體的先驅人物,也是西方小說進化過程中的奠基者,他創造了「比紀實報導還真實」的小說。他寫《大疫年紀事》時,現代預防醫學猶未萌芽,但這樣的限制,反而使得這本小說有了最堅固的瘟疫觀察之內容,也顯示出那個時代基督新教唯理人道主義的進取面貌。英國名作家布吉斯(Anthony Burgess)在為該書企鵝版所寫的導讀中,即評價它為歷史內容和創造想像兩相得兼之傑作,這並非虛譽。
十七世紀的歐洲,醫學條件落後,瘟疫到來時,「鬼神論」和「天降報應論」仍然當道,而對疫情控制,強制性的殘酷隔離則是萬靈丹。那個時代的隔離,乃是將被認為已罹病者囚禁在自家中,形同讓他們集體自生自滅。而郊區之富人或者舉家落跑,或者即在較為安全的環境下有較大的幸運。《大疫年紀事》,儘管通篇一氣呵成,但實質上則有三大重點,瘟疫初的「鬼神想像」,控制期間的實況,以及作者本身的瘟疫現象之評價。在「鬼神想像」方面,我們可發現到《新約‧啟示錄》裡的「四騎士」意象,長期以來皆主宰著西方的「災難論述」,對瘟疫尤然。倫敦瘟疫前和初,有人看到天空有劍指向倫敦城,慧尾掠空,有鬼怪穿過教堂墓園,甚至有人看到天空有靈柩棺木成行經過,小說的敘述者甚至看到一群人齊聚,抬頭望天,聲稱看到各種異象,而他抬頭則除了雲彩外,一無所見,至於民間猛出預言小冊及各類符咒,也都被作者拒斥,早期基督教唯理主義的價值觀,可謂顯現無遺。在那個時代,能有如此識見,洵屬不凡。
而在疫情控制的隔離手段上,未書之慘惻實在讓人難以卒讀,狄福廣搜具體資料,將各階段死亡數字一一彙整,將窮人被居家囚禁的慘狀,以及亂葬崗式的掩埋死者也詳細記述。還包括了社會失序的暴行、公權力執行者的殘暴等都寫進了故事中。狄福的小說寫作,其實也等於印證了「壓迫在預防隔離中」的道理。至於在作者評價部分,十七世紀英國新教的人道主義則做了詳細的舖陳。由《大疫年紀事》,現代醫學發生前的那種以道德和理性論述瘟疫問題的進步思想,可謂已極清晰。這部作品在價值上,成了後來幾乎所有瘟疫文學的共同基礎。這也是個人將《大疫年紀事》視為瘟疫文學首選作品的原因。而《大疫年紀事》,當然也可以和與其同時,被認為是英國「日記文學」最重要的倍比士(Samuel Pepys)所寫的《日記》相互參證。
繼《大疫年紀事》這種第一波紀實型文學創作後,在所謂的「現代文學」裡,以瘟疫為主題者日增。其中,卡繆之《瘟疫》;法國作家吉歐諾(Jean Giono, 1895-1970)所著之《屋頂上的騎兵》;湯瑪士曼的《威尼斯之死》;以及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九八年得主薩拉馬戈(Jose Saramago)的《盲目》,均極具代表性。在這些經典之作裡,瘟疫除了是一種現象外,同時也是隱喻或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