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仍然擅長於把最壞的情況往後拖。不斷在路上踢罐子是民主最拿手的。這也是為什麼它的路也許會被證明比我們以為的長。
文: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結論:這就是民主終結的方式
所有民主政體——所有社會——都會望向其他國家的命運,想要瞥見自己的未來。當一個對手正在邁進,我們想知道這是不是表示我們將要衰微。當另一個民主國家開始解體,我們想知道這是不是預示著我們的可能命運。民主政治對道德故事饑渴——只要這些故事是其他人活在其中。
在一九八○年代晚期,很多西方評論家都把日本看成明日之星,認為二十一世紀將會是日本的世紀。福山把日本作為闡明歷史的終結會帶來什麼的最好例子:帶來穩定、繁榮、有效率和一點點無聊乏味。但後來日本的泡沫爆炸了(與之一起爆炸的是日本的股市),未來改為是屬於其他人。日本變成了一則有關高傲自大會帶來何種危險的故事。隨著幾十年的經濟零成長和政治停滯,它帶給了其他國家尖銳的警告。任何地方的泡沫都可能爆炸。
到了二○一○年,換成是希臘亮起紅燈。歐盟不再淡定,它進入了高度警戒狀態。西方世界政治人物都把希臘作為一個例子,認為它可顯示民主國家如果不控制好債務,有可能會發生什麼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 在二○一○年就任後,用希臘的金融危機作為終極的道德故事。他在發起一個為時十年的撙節計畫時說:「從希臘,你看到了一個不面對自己問題的國家的例子。這是我想要避免的命運。」現在,十年幾乎已滿,而希臘已失去了它很多嚇小孩的能力。這個國家沒有萬劫不復。撙節並沒有帶來預期的效果。日子仍然一天過一天。
現在,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極少引用日本和希臘作為可顯示有何命運等著我們的例子。它們沒有再作為道德故事,是因為它們的信息變得太模稜兩可。日本繼續陷於經濟和政治的泥淖,但是它繼續運作著,是一個穩定、富裕和照顧好公民的社會。假設你現在抽一張大樂透彩券,上面寫著你會在人類歷史上生活的時間地點。如果彩券上寫著:「二十一世紀初期的日本。」你會覺得自己是中了大獎。希臘比較亂糟糟,但按照歷史標準衡量,它仍然繁榮與和平。情況比它嚴峻的地方多的是。它的危機從未解決,但更糟糕的情況也從未發生。
所以,我們望向明日之星的新鮮事例。中國已經取代日本,成為縈繞西方政治想像力的東方巨人。中國或許行將超過美國,但也有可能是下一個大泡沫爆炸的地方。在負面例子上,委內瑞拉取代了希臘,它當前的悲慘處境被認為是玩弄民粹主義之火的惡果。英國財政大臣韓蒙德(Philip Hammond) 在二○一七年保守黨會議演說中警告,如果柯賓當選首相,英國有可能會出現「委內瑞拉風格」的食物短缺和街頭暴動。任何可能的左派總統或總理都被比作一個潛在的馬杜洛(Maduro),一如任何可能的右派總統或總理被比作一個潛在的奧班(Orban),甚至是被比作川普。我們希望我們得到的警告是一刀切:多虧上帝恩典,民主才逃過一劫。
但諷刺的是,在政治人物不再有興趣從日本和希臘得到廉價教訓很久之後,現在的日本和希臘正是最能夠讓我們知道民主也許會怎樣終結之處。穩定的民主國家保有著擋住最壞可能情況發生的能力。希臘危機已經延後了夠多遍,以致我們必須認為,希臘經濟能維持住的可能性比我們原以為的大得多。在我走筆至此的時候,希臘經濟正在開始緩慢增長,這還是八年多來第一次。它的債務負擔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多。總理齊普拉斯比他總理任內任何時候都更不受歡迎。在希臘危機第一階段當權的中間偏右政黨也許正處於重返權力邊緣。瓦魯法克斯出了另一本書。
論生活,希臘和日本是非常不同的地方,但是它們有一些共同特徵。它們都是地球表面最老的社會:日本是極少數老年人口比例比希臘還高的國家。它的一半人口是四十七歲或更年長。兩個國家都極需年輕新血注入。在缺乏高出生率刺激的情況下,唯一解決辦法是鼓勵移民移入。然而,主張接受更多移民對政治人物來說是政治毒藥。如果他們等得夠久,機器人也許可以接手年輕人的大部分工作,讓老年人可以打電動遊戲和擔心自己的健康。我們有可能最後就是以這個樣子全變為日本人。但另有一些比較糟糕的情況。
日本同時也是地球上暴力最少的社會。它的謀殺率在已開發國家中最低。日本政界仍然充滿醜聞,從來不缺因為受賄指控而下台的政治人物,但是暴動和街頭暴力幾乎聞之未聞。政治衝突同時是狠毒和沒有利齒。希臘的犯罪率高於日本,但暴力事件仍然罕見——不只是用歷史標準衡量是如此,和歐洲其他國家比較也是如此(希臘的謀殺率低於英國) 。近十年的經濟蕭條並沒有帶來多少改變。希臘既瓦解了又沒有瓦解。它的政治轉為了惡性,但沒有轉為暴力性。看來,有些民主國家可以吸收劇烈疼痛。
日本和希臘的故事到頭來不同於我們所害怕的,甚至不同於我們所希望的。作為道德故事,它們都缺少了一些什麼。它們缺少的是道德教訓。它們的戲劇性並沒有到達一個高峰,而民主在一種蹲伏狀態中堅持著和等待著——雖然每個人在等待什麼並不清楚。過了一段時間之後,這種等待會變成整件事情的重點。最後總有什麼會出現。
當然,這並不是故事的全部。即使在西方,也有很多民主國家比日本和希臘年輕,也因此較不穩定、較沒有耐性和潛在地比較暴力性。我們並不需要到卡拉卡斯才能瞥見一個不同的未來。芝加哥便能起到這作用。
認為暴力整體而言走向下坡的主張(最著名的鼓吹者是平克〔Steven Pinker〕的《人性中的良善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對我這本書的一些論證具有奠基作用。那樣的畫面在近年來變得有一點複雜。平克的觀點有頗大比例是依賴全美國犯罪率的下降:從一九七○年代和一九八○年代的最高點下降至二○一○年代的歷史低點。但過去兩年來,美國的謀殺率上升了近一成,而這種增加集中在幾個城市:拉斯維加斯、巴爾的摩和芝加哥。在芝加哥,每個月平均有五十多人被槍殺。這個數字甚至比暴力出了名猖獗的一九二○年代還要高。
最近的暴力上升現象分布得非常不均。有些城市經驗到暴力事件的激增,但其他城市卻不怎樣被觸及。紐約在二○一六年的犯罪率仍然處於歷史新低。在芝加哥,暴力沒有波及大部分地區:在它的七十多個警察管區中,增加的謀殺案有三分之二是發生在其中五個。你有可能住在浴血場旁邊卻多少沒有受到影響。
芝加哥式謀殺並不是當前席捲美國的暴力事件中最激烈者。更多的死者是死於自殺。自殺率近十年急速上升,尤以在郊區為顯著。更多美國人開槍是射擊自己而不是射擊他人。現在,橫掃美國部分地區的鴉片類藥物氾濫比槍械暴力奪走更多生命,而且毫無減緩跡象。被車撞死的人數也在增加。結果就是讓美國成為已開發國家中第一個平均壽命降低者。去年有超過十萬美國人因為服藥過量或交通意外死亡。這是真正的美國大屠殺。
美國當前的經驗不妨稱為暴力的長尾(the long tail of violence) :暴力事件有很多,但大部分都是為特殊的群體量身訂製。暴力極少是一種集體經驗。暴力並沒有消失,而是延展開來和拉薄了,以千百種不同方式觸及個人,又讓沒有被它們影響者幾乎毫無察覺。很多這些暴力都是私人化、家庭化或機構化,發生在專門為隱瞞大多數人而設計的場所。美國的監獄系統關了超過兩百萬人,其中年輕美國黑人佔了不成比例的多數。它是一間刻意把暴力從政治變不見的巨大暴力工廠。眼不見為淨。
與此同時,某些無法形容的暴力災難的陰影籠罩整個國家。某些個人的暴力行為(特別是由恐怖份子所做出時) 被當成總體崩潰的預兆。只要走錯一步我們就可能會全部死掉。川普體現著這個現象。他經營兩種政治暴力:低層次和耗損性的暴力,表現在人身攻擊;其次是核子武器的威脅。在每一種長尾分布(long tail distribution) 中,在眾多微小事件的滋蔓中,有少數是鋪天蓋地。川普看來無法為面對日常暴力風險的千萬美國人做些什麼,卻相當能夠摧毀千萬美國人。
暴力的長尾體現著民主所受到的捆綁:它面對的威脅要不是太大就是太小。鴉片類藥物泛濫和與北韓爆發核子戰爭風險的一個共通之處,在於民主政治難以對它們作出掌控。個人和世界末日之間的空間,傳統上是民主政治擅勝場之處,但如今已變成了敵對世界觀的角力場,而這些世界觀是受到了對可能發生的最壞情況的預期的灌注。欠缺的是中層次的政治。在任何長尾分布中,中層是受到最激烈打擊者。當代民主並不例外。宏事件(macro events) 和微經驗(micro experiences) 被擠出了通情達理的妥協空間之外。當人們尋找一些也許可以促進這類妥協的機構時,發現它們已經被要不是太大就是太小的政治恐懼和挫折的牽引力挖空。
儘管如此,民主能夠撐住的理由之一是它保留著它的否定能力。挫折感有自己的用途,不管它們在其中打轉的空間有多麼空洞。當人們對於某些政治人物徹底失望時,仍然可以用其他人替換他們。可怕的領袖——中國人過去稱之為「壞皇帝」——可以用相對無痛的方式打發走。垂死的政黨最終會被載到拆車場。一種真正不專心或懦弱的民主也許會發現一個壞皇帝能夠蠶食進制度裡,變得難以趕走。艾爾多安在土耳其已經掌權了十八年,至今毫無走人的跡象。但這種事不會發生在川普身上。美國民主既不夠懦弱,也不至於不專注,不會允許他在總統辦公室待到二○二五年之後。他也非常不可能在位那麼久。
民主仍然擅長於把最壞的情況往後拖。不斷在路上踢罐子是民主最拿手的。這也是為什麼它的路也許會被證明比我們以為的長。
相關書摘 ▶《民主會怎麼結束》導讀:民主雖然容易著火,但也比任何制度更能滅火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民主會怎麼結束:政變、大災難和科技接管》,立緒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
譯者:梁永安
二十一世紀危機——民主空心化!
民主制度可以在完好無缺的情況下失靈!
二十一世紀所面對的問題是,當我們對民主的制度安排已經變得非常信任,以致在它們失去作用卻察覺不到時,民主還能維持多久?
這些制度安排除了定期選舉(它仍然是民主政治的基石),還包括民主立法、獨立法庭和出版自由。這一切都可以繼續運作卻沒有做到它們應該做的事。民主空心化的危險在於它會讓我們有一種錯誤的安全感。我們也許會繼續信賴它,向它尋求拯救——哪怕我們又會對它的無力回應呼求感到滿心憤怒。
- 民主制度已走到盡頭?
近年來,民主受到嚴峻的考驗。繼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等一連串「黑天鵝效應」接連發生後,令人不禁思考,民主制度是否已走到盡頭?
沒有任何事物、制度是永遠不變的。在某些時候,民主總是消逝在歷史的史冊中。沒有任何人(甚至是國際政治學家法蘭西斯.福山)會相信,民主的美德,會使其永垂不朽。不過,今日西方民主國家大多數公民都會認為,民主的結束,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並不會戛然而止,至少在他們還在世時不會發生。只有極少數的人會想像,或許這一天將在眼前發生。
然而就在這幾年,而且是突然之間(幾乎是憑空發生),我們卻都有了這個念頭:這就是民主的盡頭了嗎?如果是的話,我們要怎麼確定呢?本書即是幫助我們識別種種跡象,以及思考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事。
- 民主未死,只是中年危機!
事實上,在全世界,民主已經死過幾百次。我們以為我們知道民主的死亡是什麼模樣:混亂降臨,軍隊出面恢復秩序,一些年後再還政於民(不還政的情形也所在多有)。但我們也許看錯了威脅所在。
著名政治學家、劍橋大學教授暨本書作者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本書中審視了西方的政治地景,從古希臘和現代希臘的政變談到核子戰爭、環境災難和最窮凶極惡的罪行,分析民主制度遭受的威脅及其未來。
在這部銳利的著作中,朗西曼揭示出我們的社會已經發生改變(變得更富裕、年紀更長和更網絡化),不像從前那麼容易分崩離析。歷史從不會重演。代之以,制度的越來越衰敗才是民主的未來的真正威脅。
今日西方的民主制度正經歷一場中年危機,而這是場全幅度的危機。
- 陰謀論、假新聞與民粹主義
本書首先探討以往對於民主遭致失敗的種種憂慮,並思考時至今日,這些憂慮是否過時。若聚焦在政變及災難上,我們是否擔心錯了方向?我們是否該轉而將重點放在陰謀論、假新聞或民粹主義?
並進而解釋,二十一世紀的種種作用力如何「成功」使得人民失去民主而不自知。假使民主的消逝並非戲劇化的大爆炸結束,而是技術性地悄然消失呢?於此同時,民主的結束一定意味著倒退到更糟糕的狀態嗎?或是它可能促使我們前進到另一個階段?
所有政治體系都會有終結的一天,而民主的故事不會有單一的終點,民主國家也將繼續沿著世界不同時區的不同道路繼續前進。本書帶著活力和嚴謹審視問題,幫助我們思考本來不可思議者:民主的失靈在二十一世紀意味著什麼?繼民主之後有可能有更好的制度出現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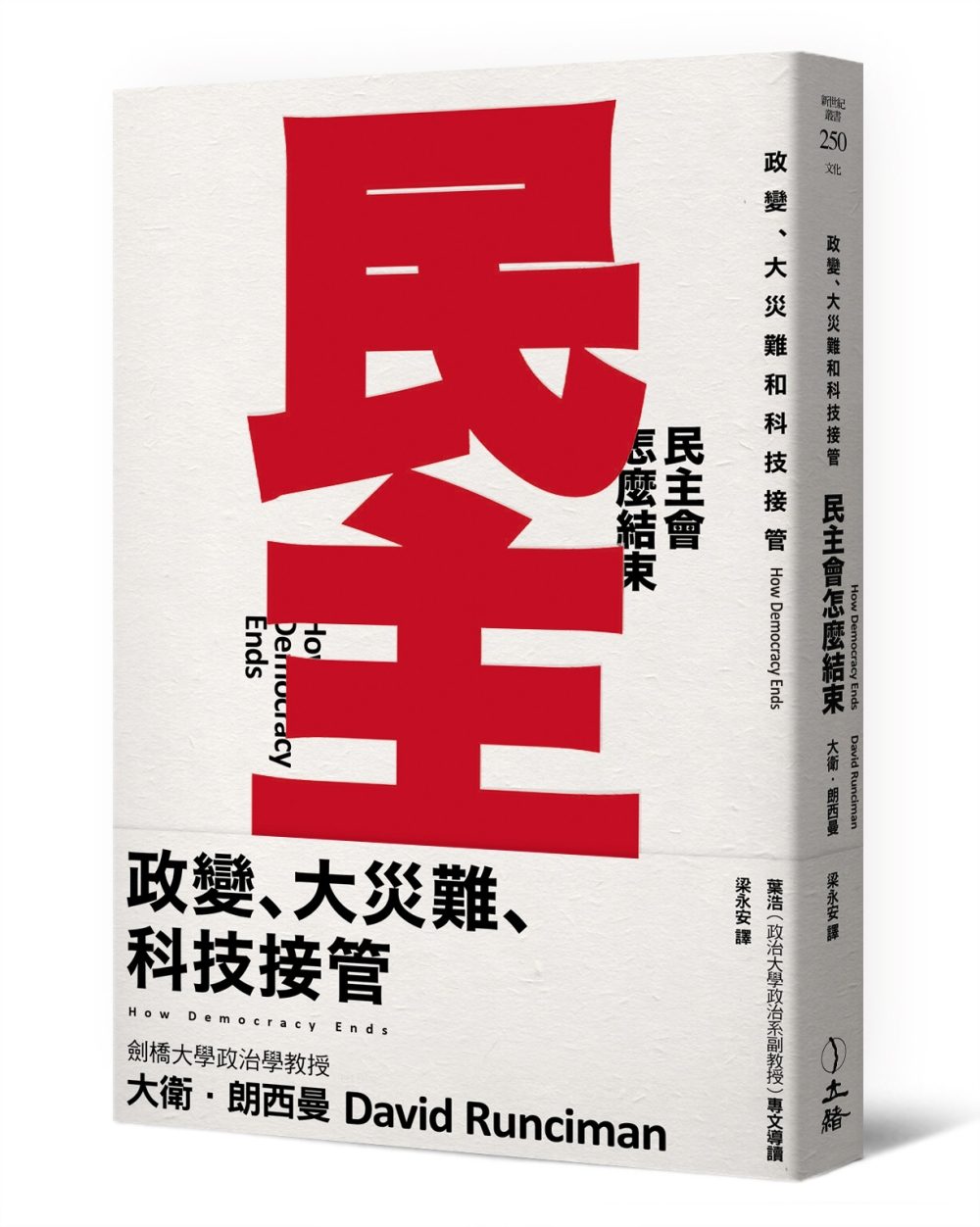 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
Photo Credit: 立緒出版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