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貢的越南人有一半住在水上,每當我有機會來到西貢,而且有一、兩個鐘頭可以打發時,我都會前往那裡欣賞一般民眾鮮活、騷動的生活景象。
文:諾曼・路易斯(Norman Lewis)
週日消遣活動
回到西貢後,我還有一天可以自由活動,然後才會真正踏上旅途。星期日的這一天,我緩步走向植物園。一群群越南美女踩著腳踏車,也和我朝同一方向奔馳,絲質長裙的裙襬在空中飛揚,讓她們個個並不像在踩踏板,而像是在飄浮。越南女子所穿的衫裙令人聯想到滿清限制令前古代中國的穿著。她們偏愛白色絲綢,而越南女子一般都非常整潔,動作也執著於天鵝般輕盈,因此整體效果極其優雅脫俗。公園裡到處可見這些飄逸的身影,成群結隊地在蔭涼的小徑蓮步輕移,間或有時髦男子相伴,只是那些男子身穿棉襯衫和短褲,頭戴呢帽,相形之下只覺礙眼。如此打扮的女子來自包括商店助理在內的上等階層。家庭幫傭,或者法國人所親切知曉的保母,穿著也一樣風雅,只是比較簡單,包括寬鬆的上衣和長褲。
令人不解的是下層階級的人都戴著圓錐形斗笠,防止陽光的傷害;反觀中產階級的人,雖然梳理著各種髮型,包括恣意流瀉至腰部的長髮,乃至燙髮,卻都不容自己戴任何東西遮陽。經過身邊時,可以見到那些女孩所戴類似苦力所戴的草帽,其實編織得很漂亮,是用一種塗有亮漆、半透明的材料所製,輕巧的編織在一個圓形框架上。每當週日散步時,她們會用兩端裝飾有蝴蝶結的絲帶繫在帽上,再在下巴處綁出第三個蝴蝶結。其效果可謂風情萬種,而我相信那些女店員或打字員一定很遺憾,只因為自己社會地位的關係,竟然無法穿戴這麼迷人的裝飾品。
在西貢這些高雅的「fêtes-champêtres」(遊園會)中,照相是項很普遍的藉口。其中有幾個適合拍照的景點,人潮不斷。像是位於一棟寶塔式建築的考古博物館附近,便有一群女子繞來繞去,等候拍照,輪到她們時即搔首弄姿,一手輕撫一尊雕龍的口鼻。另一個頗受歡迎的景點是在湖邊。湖水已然枯涸倒退,只剩幾吋深的湖水,湖面漂浮著一層浮渣所形成的綠鏽,再過去則是一片孤立的荷花,挺立在距離水面一呎之遙。有艘算是標準拍攝道具的平底船,很勉強的漂浮在水面上,拍照的女子力求平衡的站在平底船上,看來神祕而極其寂寞,攝影師則用荷葉掩飾住船首繫索,然後拍照。一旦快門按下,平底船便被拖回岸邊,接下一位少女漂浮到拍攝地點,至於拍完照片的女子則在護花使者的伴隨下,飄然而去。
「Jardins Botaniques」(植物園)所展示的自然歷史迷人,卻不致令人興奮。大眾公園理所當然不會展現熱帶自然環境中邪惡的一面,不過我還是很驚訝這裡居然沒有令人困擾的昆蟲,諸如黃蜂或蒼蠅等。有幾隻不知名的蝴蝶在周遭飛舞,形狀很像英國各地荒原所見者。園裡花不多,但是有一棵樹的樹幹和較粗的樹枝上長滿紫色花朵,花瓣厚實,質地似絨。由於是當地本土植物,因此無法查證其名稱。唯一標示名稱的樹木都是由達喀爾和馬達加斯加輸入的奇特品種,以此推測,必須前往那些地方,才能探究中南半島的植物品種。
只見最高的樹幹上,白鶴正在築巢,陽光穿透牠們淡紫帶灰的羽翼,映襯著淺綠的樹葉,形成一幅美麗、帶有濃重中國風味的畫面。在我頭頂上方的某處,一隻小鳥不停啼叫,似乎走到哪裡跟到哪裡,卻始終不見身影;牠的聲音哀切,彷彿困在一個中空巨瓶裡的布穀鳥,不斷重複著同一音符的啼聲。我後來逐漸領會,這個聲音似乎始終縈繞在中南半島的背景中。
在這些地方的越南人,儀態風度可謂無懈可擊。那是一種溫和的壓抑,有如上主日學的氛圍。只見訪客溫順的參觀圍欄中的鹿群,投幣買冰淇淋,將紙製容器摺疊好,裝入口袋;有的安靜而滿足地選擇觀賞用一部架在腳踏車上的九點五釐米手搖式放映機播放的「流浪漢」 八捲原版影片;有的光顧相命攤,由相命師量脈搏,用放大鏡查看眼球,然後宣告他們的命運;也有的在小攤前購置人造花等小禮物,攤販的淺藍色遮篷上印製著「Employez le pâté et savon dentifrice de……」(使用……牙膏)等字樣,不過只為裝飾目的,所以移除了廠商名稱。
一切都非常宜人,非常文明。
下午時分,我沿著河流往下走,感受迥然不同。西貢的越南人有一半住在水上,每當我有機會來到西貢,而且有一、兩個鐘頭可以打發時,我都會前往那裡欣賞一般民眾鮮活、騷動的生活景象。沿著河岸走動時,除了在航海俱樂部(Cercle Nautique)四十五公尺範圍內,我可從沒見過任何一個歐洲人。
他們移居水面,最初一定是因為建造一艘舢舨比較便宜,而且還可降低火災的危險,又沒有繳納地租的問題。如果偶爾想換個環境,那更簡單,只要把船開走即可。河面的溫度比城鎮低上幾度,而且只要喜歡,隨時可以跳入水中。在洗衣方面,有相關設備便於婦女使用;而只要在水裡放幾根釣線,偶爾還可以抓到一條魚。總而言之,似乎找不到任何不在水上生活的理由。如今,由於有龐大的人口生活在中國溪及其支流的舢舨船上,遂有無數水上服務應運而生。有舢舨餐館,販賣大鍋麵;販賣飲用水的小販則將水裝在塗著白色瓷釉的船底;還有各種商店,當然,還有水上魔術師。
如果想要到碼頭區,那就得沿著主要街道卡提拿街 走上近五分鐘的路。在下午五點的這種時刻,有可能要冒著無處遮蔽、直接接受陽光曝曬的危險。沿著水岸而行,碼頭工人正忙著裝卸貨物。大約四百公尺外的河對岸是一片無人的土地,白天時可以過去,一旦黑夜來臨,越盟有時就會出現,朝市中心發射迫擊砲。先前在比較遠的河岸有茅屋群聚,但法國人已經加以清除,導致難民問題更加惡化。這時刻大約是碼頭工人吃晚餐的時間,飲食攤已然擺妥一長串桌子。每張桌子上放置著三個瓶子,一瓶是虎牌啤酒,兩旁是顏色鮮豔的礦泉水。為了吸引顧客,在設計新穎的碗中,放置著半孵化的毛雞蛋,旁邊割開有小洞,讓顧客選擇其所喜愛的孵化程度。
我走到布拉吉角的一間水岸咖啡館,坐下來舒適地觀賞眼前的景象。周遭環繞的盎然生氣,和我以往所經歷的一切都不同、也更加熱切,會讓觀者學著習慣人群,習慣街上聚集的人潮,習慣娛樂場所、車站或餐廳的群眾。不過那類人群多多少少都從事著同類活動。而這裡各行各業種類繁多,我眼前大概聚集有幾百人,都忙碌於自己的營生,而大多數人都各忙各的,和左右鄰居可謂毫不相干。
近岸邊停泊著幾艘中式平底帆船,甲板上有菜園、寵物、幾隻公雞和母雞,鳥籠裡關著一隻金絲雀,還有幾口裝貨箱裡養著花。有人一直繞著甲板澆水菜園,或往裝貨箱裡澆花,或查看母雞是否下蛋。從帆船側邊開口,可以觀察船上的日常生活情況。偶爾還會見到一個赤身裸體的小孩飛出來直接往下跳,企圖降落在另一個早在下方戲水的小孩身上。
眼前還有大約五十艘舢舨,人們或躺或坐的置身船篷下方,或玩牌、擲骰子,或聊天、睡覺。有人來到岸上,牽著豬沿著水岸運動。另有十幾二十個釣客,一動也不動懶散的守著釣竿,其中最獨特的一個,是在街面的下水道出入孔碰運氣。職業漁夫則在舢舨上工作,在操縱桿尾端將三角形大型漁網垂放入水中。目睹此景,人們不免期待他偶爾能捕到一條令人驚豔的大魚;可惜事實並非如此。他們撈起的魚,沒有一條超過八公分的。捕大蝦的漁夫運氣似乎比較好。他們踩在深達膝蓋的汙泥中,用籐籃在泥水裡摸索。這是項汙穢的工作,但至少他們撈得到大蝦。
婦女們或者忙於烹調,或者忙於梳洗,全身上下無一遺漏,而且動作完美無瑕,沒有裸露任何無意展現的肌膚。不知為什麼,水上人家總是持續地挪動他們的帆船或舢舨,然後又停泊回原來的位置。在挪動間,他們經常驚險地閃避過載運來往港口和船舶間渡客的駁船。小販們不停來來去去,用饒富音律的叫賣聲,或恰如其分的敲鑼聲,吸引顧客關注他們販售的商品。
不過對許多無所事事、遊手好閒的人而言,他們不會注意到小販,而只是熱衷於觀看進行中的十幾處賭局,不時提出意見。在宛如音樂喜劇的背景中,江輪頂風破浪、緩緩行駛而過,全都有著三層甲板,高而窄的煙囪,欄杆裝飾得有如紐奧良的露台,寫滿鮮紅色的中國字。
相關書摘 ▶《東南方的國度》:中國的人造城鎮金邊,所有華麗光彩都集中在科芬特里街人潮裡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東南方的國度:一趟行經越南、柬埔寨、寮國的旅程》,馬可孛羅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聯合勸募。
作者:諾曼・路易斯(Norman Lewis)
譯者:胡洲賢
這裡,是最後的印度支那。
彷彿暗示著未來的命運,諾曼・路易斯趕在雨季刷洗走一切之前,
記錄下殖民主義在這片土地上的黃昏。
一九五〇年,前往西貢
二戰結束後,亞洲的變革迅速蔓延開來,所有國家都在戰勝氣氛與民族主義的支持下,迅速展開反殖民行動。不同於鄰近的英屬印度在戰後旋即獨立,法國人並不想放棄印度支那,並與蓬勃的抗爭勢力「越南獨立同盟會」進行長期戰事。除了越南本土的戰爭之外,柬埔寨與寮國的局勢也不穩定,槍林彈雨下的土地,失去了以往的肥沃與壯闊。在這樣的局勢下,諾曼・路易斯決定前往西貢一探究竟,展開這場動盪與危險的旅程。
不為人知的半島內陸
除了西貢與越中地區,沿著當今柬埔寨、寮國國界的高山地區,住著一群芒族、占族、嘉萊族、埃地族、苗族等少數民族。他們與越南人的關係疏遠,且在獨立的抗戰中,常常成為被犧牲的對象。然而,華麗的鼓鑼文化、盛大的宴客酒會、古老的習俗,叫路易斯讚嘆不已。他接著更跨越山脈,前往柬埔寨吳哥窟,觀賞在古城前表演的傳統舞蹈。然而,這片土地還是逐步現代化,只剩寮國,還有法國人刻意保護、略保山林的野性。
「你應該見見越南知識分子!」
在旅程往返之中,路易斯有幸跟一位年輕的越南學生閒聊,這才發現,自己聽到的幾乎都是法國人的片面之詞。於是旅程尾聲路易斯才透過線民的引導,認識一批越盟分子。他們大多一貧如洗、裝備簡單、規矩森嚴,但獨立的願望強烈。此時,戰事仍吃緊,面對法屬印度支那的未來,只能等待命運的裁決,希望這個潛伏在叢林的文明,再度光芒萬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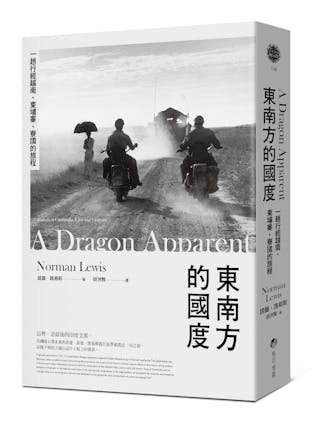
Photo Credit: 馬可孛羅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