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發現默奇森隕石運送了一種極不尋常的貨物。隕石和地球一樣古老,已經在外太空漫遊數億年,上頭攜帶了數種構成蛋白質的胺基酸,以及組成DNA的重要成分—嘌呤和嘧啶。
文:安德里亞斯・華格納(Andreas Wagner)
不妨在家裡嘗試一個令人驚奇的實驗。把小麥放入容器中,並用髒內衣封住開口靜置21天,你就會看到老鼠出現。不只有新生的小鼠,還有成鼠。別大驚小怪,起碼這是17世紀醫師兼化學家揚・巴普蒂斯塔・凡赫芒(Joan Baptista Van Helmont)的描述。(他也曾說過,將羅勒置於兩塊磚頭之間,經過陽光的照射,就會出現蠍子。)
凡赫芒不是第一位提出此假說的人,自然發生說(spontaneous generation)至少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但凡赫芒卻是最後一群提倡者之一。現在若有科學家提出小麥與內衣共同合作創造新生命,肯定被視為瘋子永不得翻身,但凡赫芒草率的實驗並沒有造成太大騷動,1644年過世時,他仍是一位備受尊敬的人。自然發生說在當時廣被大眾接受,他的實驗只是驗證了明顯存在的事。
凡赫芒過世幾十年後,義大利醫師弗朗切斯科・瑞迪(Francesco Redi)向世人展示類似的實驗如何完成。他將肉塊置入廣口瓶中,經過一段充足的時間後,瓶子裡爬滿了蛆。然而這並非自然發生的,如果瑞迪用棉布封住廣口瓶,蒼蠅就無法在肉裡產卵,也就不會產生蛆。
瑞迪促使自然發生說加速式微,17世紀的荷蘭人安東尼・范・雷文霍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也是如此。他是布商,同時是一名鏡片研磨師,他製造的顯微鏡開啟通往微生物世界的康莊大道。有段時期,微生物比可見生物微小許多,因而提供自然發生說擁護者有個完美說詞,其中如蘇格蘭神父約翰・尼丹(John Needham),在18世紀中期提出腐敗有機物創造微生物的說法。一個世紀後,路易・巴斯德的實驗結果反駁了尼丹的觀點:是微生物造成有機物的腐敗,與尼丹的說法正好相反。巴斯德將營養豐富的肉湯和周圍的空氣徹底殺菌,最終顯示並沒有新生命生成,此實驗不啻宣判自然發生說的死期。
巴斯德能夠證明自然發生說並不正確,但他與同時代的人並不了解背後的原因,因為生命的起源不是生物學家而是化學家的課題。19世紀化學家遭遇的問題,跟20世紀早期試圖了解生命創新的孟德爾主義者一樣—他們都出生太早了。德米特里・門得列夫(Dmitri Mendeleev)勉強完成元素周期表,但生命的化學仍是一片空白。基礎化學確實耗費相當時日、憑藉本事脫穎而出,成為一門令人景仰的科學,這也許是深深扎根於煉金術的緣故。進入20世紀,曾獲諾貝爾獎的量子物理學家沃夫岡・包立(Wolfgang Pauli)在第一任妻子和一位化學家相好後,曾對朋友談到:「如果她跟一位鬥牛士私奔我還能理解,但只不過是個普通的化學家……」
一個世紀後,我們曉得自然發生說面臨的巨大絆腳石,是來自生命龐大複雜表現型的可能性,或者說不可能性。即使是一個蛋白質或一個特定胺基酸序列,都不太可能自然地出現。以大腸桿菌來說,就含有數百萬個蛋白和其他複雜分子,要自然出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現代生物化學讓我們得以估算可能性,同時也推翻了複雜生物源於自然創造的說法。
這並不代表在生命早期歷史中沒有發生自然創造,生命的自然起源需要它,不過發生在比現代細胞或現代蛋白質更加簡單的形式中。地球上第一個生命形式比較類似牛車而不像法拉利,更貼切地說,像一個車輪而不是一輛牛車。即使是車輪也不是大躍進式地創造出來,而是經由許多適度審慎的步驟。時間的淤泥侵蝕了第一個生命形式的足跡,但化學家已經重建起一些步驟。化學家不只展示生命如何發生,也證明至關重要的一點:在生命出現之前,大自然的創造力就已經運用了與現今相同的法則。無論當時或現在,都需要透過嶄新的化學反應及分子才能迎來更新更進步的生命。
標示地球地質起源超過40億年歷史的冥古宙(Hadean Eon),如此巧妙的命名出自希臘文「地獄」,因為早期地球正猶如地獄,液態岩漿表面籠罩在汽化岩石大氣中。
即使在地表凝固成固態地殼後,大地仍不是個迷人的地方。若從外太空俯瞰地獄般的地球,可以看到地表千瘡百孔、布滿凹痕,數不清的火山冒著熱氣,滾燙的雨水不斷注入原始海洋,只有比現今密度大上許多的大氣壓力才能防止海洋被煮乾。無庸置疑,只要呼吸一口便足以讓你命喪黃泉,大氣中的毒性來自達致死量的二氧化碳及氫氣。尋找躲避處算是上上策,因為在晚期重轟炸時期(Late Heavy Bombardment)許多巨大的小行星猛烈撞擊早期地球。雖然這些古老的劇變痕跡大多因地表動蕩不斷而消失,但你可以在夜晚看見月球上巨大的隕石坑,留下的傷疤仍能讓人不寒而慄。我們從古代岩石裡緩慢滴答作響的化學時鐘獲悉地球年齡,像鈾這類放射性物質的衰變記錄了古老的歷史。
當最壞的時期過去,最值得注意的是生命出發的速度快得驚人。大約在38億年前,也就是地球誕生僅僅幾億年後,不到現今歷史的十分之一,第一批微生物化石就出現了。即使接近38億年前的不可思議分界線,古早代謝產物的痕跡便以碳的較輕同位素形式,出現在西格陵蘭的岩石中。生命沒有浪費任何時間,幾乎是以飛快的速度出現,這告訴我們生命起源和背後的創新力或許沒那麼困難發生,而且這種創新能力可能和生命本身一樣古老。
地球早期生命起源顯然需要一套化學理論來說明。最早之一是「原始湯」(primordial soup),通常歸功於亞歷山大・奧帕潤(Alexander Oparin)以及提出現代演化綜論的豪耳丹,他們在1920年代提出此理論。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擁有先見之明的達爾文比他們早半個世紀就已經有這個想法。1871年,達爾文在寫給約瑟夫・道爾頓・胡克(Joseph Dalton Hooker)的信中推測:「假如(噢,多麼大器的假如)我們能設想在一些溫暖的小池塘裡,加入各種氨磷酸鹽、光、熱、電等等,經由化學反應形成蛋白化合物,並準備進行更複雜的變化。」同時,達爾文也給了我們一個很棒的理由,說明為何今日我們可能會失望地凝視這樣的溫暖小池塘:池裡的物質可能被現今的生物「吞沒或吸收」。
數十年來,原始湯一直都只是推測,直到1952年,獲得諾貝爾獎得主哈羅德・尤里(Harold Urey)在芝加哥大學實驗室的研究生史丹利・米勒(Stanley Miller)的鼎力相助。根據對早期大氣中氣體成分的推測,米勒將這些氣體密封在一個容器中,以大量電火花模擬原始閃電給予衝擊,並用大量冷凝水模擬降雨沖洗混合物。幾天後,通常由生物創造出來的許多有機分子出現在米勒的微型世界中。這是名留青史的發現,展示在動盪的地球生成初期如何從無機物質產生有機分子。米勒的原始海洋不只製造出有機分子,也創造了現代蛋白質的基本建構組成,例如甘胺酸(glycine)和丙胺酸(alanine)等胺基酸。隨後的實驗繼續製造了許多其他建構生命的原料,包括醣類及部分DNA。更重要的是,米勒的實驗將生命起源從哲學推測轉往邁向一個艱難、實證的科學。
1969年9月,全世界獲悉米勒在1952年不知道的事:生命分子能夠在比地球早期更不利的環境裡出現。那個九月,距離澳洲墨爾本北部約160公里、人口約數百人的小鎮默奇森(Murchison),一顆爆炸的火流星短暫地在天際創造第二顆太陽。隕石破裂後留下一道拖曳的煙塵和較小的碎片,其中最大一片墜落在穀倉,幸好並沒有釀成災害。這場宇宙意外發生在人類第一次漫步月球的兩個月後,當時的科學家都熱衷於研究來自外太空的隕石。
熱潮消退後,科學家發現默奇森隕石運送了一種極不尋常的貨物。隕石和地球一樣古老,已經在外太空漫遊數億年,上頭攜帶了數種構成蛋白質的胺基酸,以及組成DNA的重要成分—嘌呤和嘧啶。後續的研究運用21世紀的光譜學,證實了隕石含有超過一萬種不同的有機分子,雖然其中許多成分的含量極為稀少。
值得注意的是,默奇森隕石並非大自然的惡作劇。隕石墜落地球的事件層出不窮,數不清的各種岩石穿透天際,把有機物質運送來地球。幸好我們不必痴等另一顆隕石墜落,因為宇宙中的分子會藉由吸收或發出輻射來顯示自身的結構,經由電波望遠鏡高敏感度的大耳朵,就可以聽見眾多星際氣體雲中數百種不同有機分子不斷對我們喃喃低語。事實上,這些分子可是在吶喊,因為星際雲中四分之三都是有機分子,其中含有生命的關鍵成分,例如甘胺酸。順道一提,星際雲中含量最豐的三原子分子就是水,這不啻在宣告我們和我們的星球是多麼非比尋常。
宇宙中,建構生命最簡單的組成無所不在,來自外太空的分子可能就此在地球播下生命的種子。隕石和彗星(尤其是早期撞擊地球的)釋放出比現今地球海洋總量多十倍以上的水,以及比現今大氣高千倍以上的氣體。更至關重要的是,它們也提供了豐富的生命資源,也就是我們在星際空間中發現的有機分子,數量多到令人難以置信,至少十兆噸之譜,或許已有高出這個量幾百倍的有機碳從外太空進入我們的大氣層,至少比現今循環在活細胞中的碳含量多十倍以上。彗星後面拖曳的塵埃,其重要性亦不遑多讓。這些塵埃通過地球軌道時,不像巨大隕石在墜落過程中造成的白熱高溫破壞了部分有機分子,彗星的塵埃以看不見且持續不斷的生命種子雨披覆地球。或許我們真的是由星塵所組成。
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大多數生命分子是在外太空、抑或在地球上創造出來,但無論如何,這些發現包含幾個簡單而重要的課題:第一,生命分子會在適當的環境裡自然出現;第二,此環境不需要是達爾文所說的溫暖池塘,也不是宇宙中鄰近且非常特別的地方,它可以在幾光年之外,或是像星際氣體般無所不在。
第三是有關創新的課題,我已經提過了,到今日仍屹立不搖:創新圍繞著新的分子和創造它們的反應。想要了解創新力,我們就必須明白這些分子的起源。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生命如何創新:大自然的演化創新力從何而來?》,馬可孛羅出版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關鍵評論網》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安德里亞斯・華格納(Andreas Wagner)
譯者:詹佳蓉
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的百餘年後,始終存在耐人尋味的一道難題:
自然界中的「創新」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1859年,達爾文發表《物種起源》,他的天擇理論解釋了有用的適應性如何隨時間被保存下來,但同時也製造了演化的最大疑問:「生物的適應性是怎麼出現的?」
地球上第一個生命誕生至今,38億年間發生的隨機突變,真的可以為翅膀、眼球、偽裝、乳糖消化、光合作用,以及其他自然創造的驚奇負責嗎?假若答案是否定的,那麼演化的速度和相對效率背後的機制又是什麼呢?
當年達爾文不知道什麼是突變、基因、DNA雙螺旋、轉錄與轉譯作用、DNA定序,也缺乏遺傳學、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甚至處理大量資訊的知識和技術,但他早在160年前提出的遠大洞見開啟了生物學百家爭鳴般的精采發現──如今,我們終於有能力朝「生物適應性的出現」這個巨大謎團靠近了!
全球知名的演化生物學家安德里亞斯.華格納憑藉超過十五年的研究,呈現出達爾文理論遺失的拼圖。利用早期科學家意想不到的實驗性及計算性技術,他發現驅動適應的不只是偶然,而是一套法則,允許大自然在隨機變異上花費的小部分時間裡,發現新的分子與運作機制。
一絲不苟地研究、仔細地論證、充滿感召力地寫作,並列舉了五花八門又迷人的實例,《生命如何創新》獻上生命豐富多樣性謎團的最後一片拼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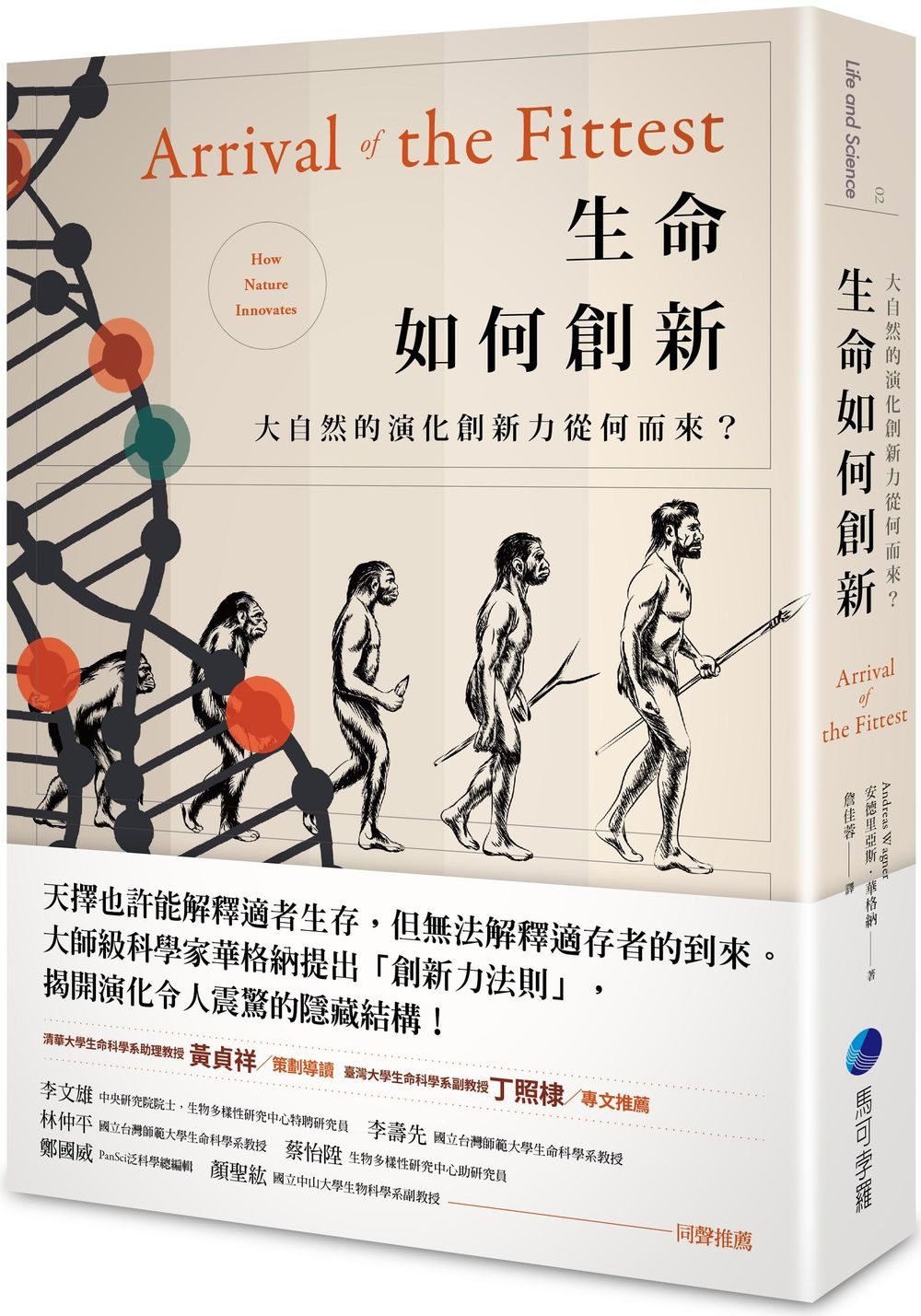 Photo Credit:馬可孛羅出版
Photo Credit:馬可孛羅出版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