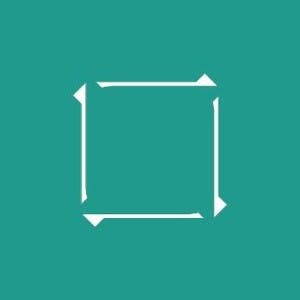香港主流劇場主要分為應用面向、娛樂面向和美學探索面向。應用面向就是以戲劇作教學,例如在學校做school tour、教中文;娛樂面向可能是音樂劇,或者以故事為本的寫實主義戲劇表演,目的為享受故事而非革新或反思劇場美學;另一樣就是劇場作為美學發展的面向,比如鄧樹榮、何應豐,以有別於講故事的方式來發展美學。現在主流劇場是這三個面向,全部都有資助的,好處是能夠讓藝術工作者維生,壞處就是缺少了政治面向,劇場作為政治和交流的面向是缺乏的。
時間:2023年12月2日
地點:Google Meet
主持:鄧小樺(《方圓》總編輯,香港文學生活館總策展人。下稱「鄧」。)
與談人:
- 張婉雯(香港作家。下稱「張」。)
- 黃飛鵬(本地獨立電影導演、監製。曾入選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之亞洲電影學院,並榮獲特出表現獎。為電影《十年》執導短片《冬蟬》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下稱「黃」。)
- 謝昊丹(參與劇場演出逾十年,現為自由身演員、戲劇教育者,亦有編導作品。關注不同能力人士、性小眾、病人權益等邊緣身份議題,曾為醫療事故記錄劇場《Closed File》擔任導演。下稱「謝」。)
整理:李卓謙
黃:回到《紅樓夢》,就是當他去到沒有錢的瞬間,那瞬間對我來說挺特別,突然的隕落,當然也有一些前奏,但是那隕落是突然間,家道中落,突然間「閂門啦,拜拜」那種狀態。我覺得以文藝的方法生活,大家都會有這個狀態,因為我們長期在比較底層的金錢崗位裡,我們經常都要追問「你是不是真的喜歡?還是為了錢?」我覺得這些思辯令我很累,經常要想這些是很累的,變相我覺得我能夠以我喜歡的東西謀生,我喜歡的東西多一些,範圍就寬廣一點,所以我沒甚麼勞動感。
鄧:「富貴閒人」的感覺。(黃:對。)在我成長之中,十八歲之前,除了《紅樓夢》之外,我應該沒接觸過其他東西那麼清楚地教我分辨,甚麼是別人要你做,甚麼是你自己覺得有趣去做,教我要好像寶黛那樣追求喜歡的東西。那個教育其實是來自《紅樓夢》。
婉雯又是怎樣想?我覺得讀中文有個趨向穩定的結構,只要讀中文出來做老師,基本上就是個穩定的中產人生,所以中文好是有種拉力,拉你去穩定的地方。不知道你怎麼看?在生命或成長中,跟主流價值的切磋是怎麼樣?
張:我想是相對的,我不會覺得自己很另類。例如說我中學時看《紅樓夢》,可能只不過是在裡面追求ego,例如說林黛玉其實是個ego超大的人,對十多歲的中學生來說,那個階段你就是在尋找或建立自己的ego。林黛玉對當時的我來說,就是個能夠投射的形象,例如說她有文學才華,當時我除了中文其他都不擅長,你可以說有中文的才華,然後她的性格超敏感,她能感受到別人感受不到的,在中學階段每個青少年多多少少也有敏感的時候,多多少少會將自己投射進去。林黛玉是個骨灰級文青,我們這類喜歡讀中文、中文成績比較好,看到書裡的骨灰級文青,就覺得「正啊,這是我偶像」,多多少少有這樣的想法。
但到後來,《紅樓夢》對我來說是美學的參考書,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教書的生活相對穩定,但始終不是上流社會,不是真的很有錢,真的有錢亦不代表你有品味。賈寶玉應該是第三代,有句說話叫「富不過三代」,我覺得品味是跟錢有關的,你自小在物質生活優越的環境長大,不用憂柴憂米,不用理會那些俗氣的事,那你就去追求藝術,追求品味。
我現在看《紅樓夢》會看它的儀式,例如《紅樓夢》裡的除夕是怎樣,他們怎樣佈置、怎樣行禮,穿甚麼衣服,過中秋又要做甚麼,碗碗碟碟有甚麼特別,這些他都描寫得很仔細,這些都不是中產階級的層面,而是上流社會的層面,而上流社會裡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這種品味,這些都是積累下來的。如果你還在賺錢,你未必有那樣的閒暇,你有錢又不用去賺錢,像賈寶玉他們,你才會有這心情,要不就好像賈母,退了休,甚麼都不管。就是那種儀式感,其實儀式感在繁忙的生活裡是很奢侈的事,我現在就會喜歡看這些。
鄧:婉雯一方面固然有貴氣,另一方面還有頹氣。我記得有次我們做網上對談,完結後她忽然問,大家是不是都只打扮上身,下身跟我一樣穿短褲。應付了上半身,下半身就可以頹,她對這件事特別有感。你是怎樣磨合「貴」和「頹」?
張:看你怎樣看「貴」跟「頹」吧。在賈政的眼中,賈寶玉也很頹,不工作,不讀書,只玩樂。在讀者眼中,這些是貴氣,你根本就不用工作,為甚麼要做,為甚麼要作賤自己?看你怎麼看。剛才阿丹說他讀書時的事,我想問他是讀A-Level還是DSE?(謝:DSE。)我自己讀A-Level,我教的學生讀DSE。我覺得DSE就似科舉,A-Level好一點,DSE真的是科舉,我想說的是,如果你要考DSE,你想中文成績好的話,跟讀《紅樓夢》是沒有關係的。因為DSE是教範文,將自己套入marking scheme。
謝:某程度我就是不太喜歡這種狀況,我才會去讀其他類型的書。
張:《紅樓夢》對我來說是美的東西,它是不切實際的,美的東西是不切實際的。如果我只是想提升DSE成績,我不如去找補習天王,一定比你讀《紅樓夢》好。但我就是不想,我想要一些毫無目的的東西,我享受毫無目的的過程,我覺得那個東西很美,對我來說《紅樓夢》就是這樣的存在。
鄧:也想起一點性別問題。我們女生小時候讀《紅樓夢》會把林黛玉當成role model。我想可能男生是不會的。
黃:我讀的時候其實挺討厭林黛玉。(張:覺得她煩。)覺得她好煩,好扭擰。在某些角度我會替她難過,不如妳嘗試走前半步?不如試試說出來,先不要哭吧?我很認同剛才說黛玉ego很大,是很能看見的,因為我自己是個相對ego小的人,我看到她就會覺得好麻煩。我又未至於不當她是role model,我反而覺得,在生活裡看到很多類似的人,無論是寶釵、寶玉,其實你都會在身邊的人裡看到一些影子,姑勿論書裡那些攀炎附勢的人。我覺得最重要的不是那個人物有沒有參考價值,而是他能夠被生動地描述,這對我來說是很fruitful的。

青春烏托邦與文藝社團
鄧:大家說了一些文藝起點,接下來我將那個「文藝夢」擴大一點,從文藝團體、文藝社群互動的記憶、經驗或故事來談,可以是正面經驗,也可以是負面經驗,文學組織的負面經驗應該多於正面經驗,不如由飛鵬先講。
黃:我覺得這是文學和電影很大的分別,文學可以一個人做,電影不可以,接近不可能。變相我們很習慣與人工作,當然也有擅長與不擅長。我覺得,有某些拍攝精神能夠帶到生命之中,拍攝時候遇到問題,基本上是每天、每時每刻也會發生,突然下雨,某件衣服沒有帶,那怎麼辦?壞事發生的頻率太高。阿丹做劇場,排練和準備時間可能很長,拍攝是沒有的,三天後就要拍了,大家就立即準備,其中總會有甩漏,然後我們就會衍生出一種個性,就是不太追究哪個做錯,追究已經沒有意義,只是想解決問題。對我們來說,麻煩事是很貼身的,變相在組織上強烈一些。
我自己有些好的經驗,最初我們辦學生電影節,那時很重要的契機是,覺得在學生時代被嘉許,對學生有很大推力,因為我在學生時代不會預期有人看我的作品,不會覺得別人會認真看待那些作品,不覺得別人會把你當導演、編輯、攝影,一來到商業世界、現實社會,你就是個intern,當你還是學生時,如果有一個電影節認真地跟你說,你的作品非常有前瞻性,評審看完都覺得很有趣,在百多套作品中脫穎而出,這種尊重,對我們來說很重要。當你還年輕時,有人扶你一把,告訴你「畀心機繼續拍」,令你覺得,我可能真的可以嘗試一下。所以當時就加入了這個團體,辦學生電影節,雖然後來就慢慢淡出了,但那對我來說仍是個好的經驗。當你遇到那時的學生導演,知道他仍然在這行業裡繼續前進,都會覺得很開心。
鄧:為甚麼忽然想拍《紅樓夢》短片?
黃:係傻仔,完全是傻仔,沒其他原因。那時想參加坂本龍一的比賽,我對攝製隊的說詞是,這件事沒有錢的,一元都沒有,但你可以試想,我們一起做一件事浪費他十分鐘,他看完就當我們贏。如果可以用坂本龍一的歌做配樂,那說甚麼好?當時他的唱片,有幾首歌都給我輪迴的感覺,有點像我讀《紅樓夢》時那種墮落凡間、輪輪迴迴的感覺,好像之前所說,伊底帕斯王一早就被決定了命運,《紅樓夢》也一樣。於是就組織了一班人去玩。
拍這部片有個難處是,我覺得《紅樓夢》裡很多東西都是真亦假時假亦真,於是我們就想,在片裡的object,是不是真的呢?開始想很多不同的方法去mimic,這件事很麻煩,但也挺好玩,去到某程度我也放棄,不要搞了,但美術說真的不可以放棄,倒過來比我還上心。感覺是大家一起玩。
鄧:關於阿丹我特別想知道「酒讀哈維爾」,出現「織梭」這個計劃後,我才知道有這麼正的東西。參加讀書會再創作,我們這些老人家已經無時間參與這種活動。讀書會在我的記憶中,只有讀研究院時才能維繫,如果要上班,就已經不太可能參與,可能我太忙了。讀書會是某種小眾的狀態。我想知道這個curation,和你們相處的方式是怎樣。
謝:我先略談為甚麼會有這件事,和它有甚麼價值。香港主流劇場主要分為應用面向、娛樂面向和美學探索面向。應用面向就是以戲劇作教學,例如在學校做school tour、教中文;娛樂面向可能是音樂劇,或者以故事為本的寫實主義戲劇表演,目的為享受故事而非革新或反思劇場美學;另一樣就是劇場作為美學發展的面向,比如鄧樹榮、何應豐,以有別於講故事的方式來發展美學。現在主流劇場是這三個面向,全部都有資助的,好處是能夠讓藝術工作者維生,壞處就是缺少了政治面向,劇場作為政治和交流的面向是缺乏的。
在近年,我們留意到社會有些trauma,少了公共空間,究竟怎樣維持交流呢?於是我們做一些私人讀書會或讀劇,我們的讀劇和我剛剛所說的三個面向不同之處在於,我們一半時間讀劇,另一半時間討論和交流。這在劇場是少見的,因為主流觀眾都期待被餵,你排了一套戲,好不好看?有沒有娛樂性?但是我們在這些讀劇會、讀書會中,大家不只是來看演出,事後需要交流、談自己感受。
鄧:怎樣選擇對象呢?
謝:近年哈維爾的文章大受歡迎,例如〈七七憲章〉,哈維爾另一個身份是劇作家,所以我們選他的劇本來讀,發現他不只在理論或政治上給人啟發,劇本能夠將很多人帶入那個時空,一起去面對當時的處境,好處是我們不是將香港黃藍壁壘分明的狀態帶出來,因為這樣可能會造成很多傷害。我們透過外國文本,打開自己,去理解更多不同取態的人,這就是文學作品帶給我們的空間和距離。所以哈維爾比起當時的一些香港劇本,可能更加適合。
鄧:讀劇是排演形態的讀劇嗎?
謝:是排演的,不過沒有台燈聲,就坐著讀對白,那兩個演員有排練,也有一點空間設計。劇場可以用文學來處理,也可以用劇場性來處理,我們抽走所有劇場性,集中在文學和當時的劇本處境。觀眾群和我平時在劇場看到的很不同,多了很多讀書人和知識份子,後來我分析就覺得,我剛才說主流的劇場要不拿來做教育,要不娛樂,要不就是探索舞台美學,對於讀書人,這三樣東西可能都跟他們本身關注的思辯無關。某程度上這班觀眾,跟平時在劇場那些很不同,他們會探討政治的不同取態,或者有甚麼歷史可以引用到香港的狀況,有沒有東西可以啟發我們,我們找了羅永生和許寶強合作,吸引一些理論比較好的人來參與我們的project。
當時的迴響都不錯,有些人都哭了,不是由於劇好看所以哭,而是我們能夠將當時捷克的處境,套用在香港的狀況上,然後幫大家打開這個話題。某程度上解決了某些人的trauma。
鄧:抽走劇場性,留下文學性,採用地下、私人的方法進行,其實它反而達到公共性,公共空間萎縮之後剩下的公共性。我覺得這個很inspiring。我們拿走某些外在的東西,直奔核心,思考大家到底需要甚麼。

圖片由作者提供
【加入關鍵評論網會員】每天精彩好文直送你的信箱,每週獨享編輯精選、時事精選、藝文週報等特製電子報。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立刻點擊免費加入會員!
核稿編輯:TNL 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