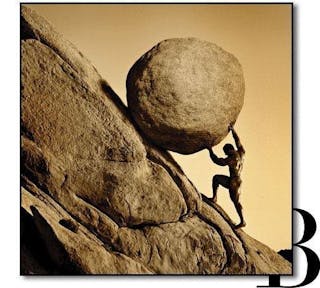為何漁業署一年花幾千萬派出觀察員,但蒐集的資料卻無法公開,也無法作為裁罰漁船不實申報的依據?原因是,擔心觀察員在船上遭遇危險、或是之後船東拒絕讓觀察員登船,造成遠洋漁船的觀察員涵蓋率不足,對國際組織無法交代;再者,某些遠洋漁業公司的政治背景驚人,漁業管理單位得小心謹慎。
台灣看似民主跟法治的社會,但其實有時感覺奴性跟人治成分還是相當重。我們喜歡講人情,也喜歡專漏洞。
有一次,新的一年,單位內有申請新的停車證,但是車位有限,於是只能用抽籤的方式。我並不常開車上班,自然沒有停車需求,但同事就來拜託我要登記,如果到時我抽到車位他沒抽到,可以轉讓給他。也沒多想,就答應了。後來,果真我抽到的車位他沒抽到,於是就私底下講好轉讓給他,他也先去預繳費了。
但像這樣的抽到轉讓的case其實很多,加上有不少同事在新年考上其他單位離職,車位居然又多了出來,於是,我同事就這樣候補到了。既然自己候補到了車位,他認為就不需要我的車位了,於是請我去辦理註銷退費。
哪知,負責停車位分配的業務單位有規定,除非離職或特殊原因,否則是無法辦理註銷的,該單位主管還對我曉以大義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幫人家登記的,但如果依照一般規定走,其實大多數人都申請的到車位,不用這樣後補,多了很多行政程序。」想想,也沒錯,為什麼大家都要鑽這種漏洞呢?我自知理虧,摸摸鼻子就走了。
不過,我同事並沒有就此放棄,他透過關係找了權力人士打電話給停車業務單位的主管,對他施壓,要求將車位登記費用退還給我,就因為這樣,我又被找去曉以大義:「這次就先退費,以後內部的事情內部解決,不要找外面來施壓」。
當時的我,真是百口莫辯,一肚子鳥氣只能吞下,只能怨恨自己,當初為什麼賣人情鑽這種漏洞,另外也很深刻體會到,台灣,真的不缺法條/規定,而是不按照規定走的人,很多,找關係的人,很多,而且很管用 …
政府理當處理的是「眾人」的事,但現在「眾人」可能得定義為:有管道的人。有管道找到民代,就能處理一下;有管道找到行政首長,也能處理一下;基層公務員其實是政策執行的最小單位,在執行上除了依法行政,理應能透過自己的裁量判斷去審視每個案件的輕重緩急,但當有管道的人關心某個案子時,就會被逼要調整優先順位,有聽過承辦人因為詳細審查每個程序卡到財團的開發案,遭到調動職位;更有嚴格執法的警察人員,被長官說不要衝那麼快之類的傳聞。
或許,像唐湘龍講的一般,這是個沒錯也要馬上「裝錯」的時代,只要被「瘋狗浪」頭的政媒鎖定,請記得:不會「裝錯」就是「大錯」。於是,政府施政不問邏輯,只問風向。周星馳「九品芝麻官」裡風往哪邊吹就往哪邊倒的「尚書大人」,看來離我們並不遠。
行政專業遠去的年代
為了理解政府是如何走入政治決定專業的過程,特別訪問了曾擔任省政府時期水利處長的李鴻源教授。他說,關鍵的問題就在公務員逐漸變得沒有專業。過去的技術官僚,實務經驗相當強,廠商要偷斤減兩沒那麼容易;但是,這樣的強項在公務員成為發包工具之後就漸消失。
原因有兩個,在教育養成過程中,以學術至上的高教系統,讓技術專長的老師無法獲得晉升,越來越脫離現場的結果,讓學生也缺乏實務經驗。李鴻源說:「聽到研究生考上公職要去報到,我只說了一句話:你什麼實務經驗都沒有,敢去嗎?」
不過,事實上,沒有經過任何業界洗禮,沒有任何實務經驗的公務人員在目前政府很多,學校實務訓練不足加上學生一窩蜂投入公職考試的結果,我們養成了太多紙上談兵的公務員,在工程案件中,這些公務員成為廠商眼中的小白兔,很容易掉入陷阱中,或是變成太過依賴特定廠商的情況。
行政專業遠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務官過度介入事務官的人事運作。過去,政務官負責政策走向,涉及行政、人事的部分,則委由事務官負責。事務官畢竟在單位時間較久,了解內部行政文化,也懂得知人善任。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政務官將事務官的調動升降當作個人政治資源,專業及工作能力不再是陞遷的主要考量,甚至,某些單位中,想升遷、調任,都得找民代關心一下,才可能卡到位。長期下來,常任文官對於陞遷要嘛看淡,要嘛就得走向關係考攏這一套。整個文官體制的價值崩毀。
台灣怎麼領到漁業黃牌的?
►歐盟對台灣非法漁業祭出「黃牌警告」 若未改善損失恐上看5億
專業角色逐漸失去的結果,公務員轉型成為寫招標計畫的高手。然而,因近年來考公務員成為顯學,許多畢業生初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公務員。沒有業界經驗,在標案撰寫時必然會遇到瓶頸,尤其是工程標案,缺乏現場經驗的承辦人,必須倚賴廠商提供相關材料規格、價格、數量、設計圖等做參考,自然而然就會與特定廠商交好。
另外,與產業界互動密切的單位,長年與業者進行市場情報交換,管理措施意見交換,政策擬定前也需要找業者了解業界反應,所以難免會與某些廠商走的較近。排除實質的利益交換,在台灣政通商的情況下,這些產業密切的官員能夠上到一定位置,必然需要掌握大老們的心性,避免政策對於這些產業衝擊太大。而官員本身也因進退得宜、廣結善緣,在晉升之路上相形助益。可以說,某些隱含在圖利行為定義之外的個人利益,在這樣的模糊地帶被滿足了。管理及政策工具,提供了鞏固權力的附加價值。
這種遊走模糊地帶的裙帶關係,在資訊不透明的狀況下,特別容易產生。比方說,我們的漁業管理,因為漁獲資料蒐集困難、不確定性很高,造成官員進行管理時經常難以判定業者填報資料合理與否。這種情況下,高度依賴行政裁量權去認定,就很有大的迴旋空間。
資源管理本來應該是與科學資料高度相關的,要有足夠的資訊,才能知道哪些魚類資源不足了,要設定捕撈限制量、或限定漁業捕撈期間。然而,要調查海裡的生物資源是很困難的,很多資料來源必須藉由漁船提供。因此,漁獲資料是否確實申報,就是漁業資源能否妥善管理的基礎。
漁政單位有漁業年報,呈現每年各種水產捕撈的產量資訊,學術界進行資源評估時,也是參考年報中的資訊跑模式確認水產的資源狀況,再去制定總量管制、或是針對季節或是體型大小限制的捕撈管制措施。
不過,台灣在漁業管理的態度上,一向採槍口一致對外的做法。怎麼說呢?當國外有要求,我們才會乖乖的申報。曾經在2005年時,台灣大目鮪魚的捕撈配額遭到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國際委員會 (ICCAT)砍了百分之七十,原因是台灣漁船偽造捕撈資料。2015年,台灣又因為未妥善管理「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的漁船,而遭到歐盟舉黃牌,若六個月內未改善會遭到貿易制裁。
台灣漁獲資料未誠實申報的情況,其實熟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即使漁業署配合國際漁業組織的規範,派了觀察員上遠洋漁船進行漁獲資料的登錄,但是漁業署本身也清楚,觀察員的資料僅能做為內部使用,而「加工完成」後的資料再送出給國際漁業組織。
為何漁業署一年花幾千萬派出觀察員,但蒐集的資料卻無法公開,也無法作為裁罰漁船不實申報的依據?原因是,擔心觀察員在船上遭遇危險、或是之後船東拒絕讓觀察員登船,造成遠洋漁船的觀察員涵蓋率不足,對國際組織無法交代;再者,某些遠洋漁業公司的政治背景驚人,漁業管理單位得小心謹慎,深怕弄出難以收拾的場面。原來應該肩負管理責任的行政部門,卻因為「特殊性關係」而舉步維艱。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之瑜